《如夢蘇州二十年》[如夢蘇州二十年] - 如夢蘇州二十年第10章 2006在線免費閱讀(2)
謀。
2005年5月,當飛機又一次降落在海浪機場,我並未有平常的踏實感,我已習慣飄着,我既在這裡,也在任何地方。我曾在愛欲里苦苦尋覓的,一體的、自我棄絕的、靈魂全息投影般的依戀,就這樣漫不經心地在眼前的「事業」里滑過。抱歉,我只能暫且稱其為事業:令神經再度興奮的情感**中的、必須全神貫注的事業。我至今仍無法得知,涉密組織是如何在人群中將弔兒郎當的我標註的,但我似乎懂了我這樣的人的激活密碼:在唯物主義世界觀剷平個人英雄主義的地基上,在物慾橫流催生的普遍的虛無主義大背景下,我們需要無限想像力加持下的瘋狂,像極了大航海時代的海盜,去世界的盡頭,不管路途有什麼。一句話,我給我的自我洗腦了,一夜之間,我這個六線城市的浪蕩子,突然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崇高感。
深圳之行又像是翻譯外掛,我和主任一下子就擁有了同一套語言。在海浪機場的候機大廳,我還算精準地問了兩個問題:1、缺失的關鍵部件是原件帶回?或其圖紙?皆可?2、Q-1606是臨時的還是終身的?主任用兩個問題的合併給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,他一貫如此:編碼是非常規狀態下你的名字,我們是本家,Q是姓錢,1606是……(他掏出一個小本子)哦,可以是「琚」,也可以是別的什麼字,你自己查吧,參照四角號碼查字法。比如說,非常規狀態下你的名字是「錢琚」,那麼必要時組織會在全球範圍內過濾關鍵字打撈你,至於任務,隨機應變,你知道的。之所以選在機場見面,是我等下要直接飛去上海,於是開門見山說:「此次的任務報酬是多少?我想預支50萬?」主任定定地看着我說:「100萬,人活着回來就算完成任務。」「明白,我得先飛上海,再去哈巴和兩位兄弟匯合。」「情財權藝宗,關關難過關關過!」主任拋下一句,輕飄飄地走了。
這幾年接連發生的事情,讓我偏離我的信念基礎越來越遠:我所受的教育,我將計就計的婚姻,我半推半就的國企身份。一句話,父輩們點頭稱讚的,一切的所謂「精明人的選擇」,然而就在這看似安穩平和的表象下,我竟然漫不經心地走上了一條堪稱奇蹟的道路:在這條多指向的、無目的、虛無或者神秘主義的道路下,「蘇州」的意指到底是什麼?我仔細搜尋從高中到大學,從大學畢業到各奔前程,從南北分別再到此時此刻,我和麗塔的每一次相處和交談,到底是什麼樣的「量子級」的碰撞,才讓我對「蘇州」有如此執念?而我此前加總起來,在蘇州停留不過區區半天的時間。這的確令人費解,尤其是在接連的刺激和自我洗腦的神經組織內,已經在唯心主義的幻境越飄越高的不堪一擊的此在。麗塔那裡,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!如何不讓她看出,我是來找答案的呢?在飛機上我冥思苦想着,不知不覺睡著了。
浦東機場。麗塔黃色的頭髮在人群中很顯眼,我揮了揮手,大踏步朝她走去,來了一個樸實無華的俄式熊抱:「幾年不見,你還是那麼漂亮!」「你倒是壯實了很多。」「不再是你嫌棄的那個瘦骨嶙峋的人了!」「我嫌棄過嗎?在哪啊?」我發覺我們都臉紅了…「我……在飛機上,做了一個夢…啊…對我餓了,我們去找點吃的。」「走,帶你去巨鹿路!」
「上次電話說過房子的事,這次看來真的要拜託你了。」
「只要你是當真的就好,你這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。在班級群里快成了頭號神秘人物了。」
我低頭沒立即搭話,把一串賬號給主任短訊發了過去,然後看着她說:
「六線城市,人情關係更密切,聽說我快鬱悶了,有挖我跳槽去私企的,有推薦我考公務員的…這不,還找了個師傅練了半年肌肉。其實就是無所事事,能閑出個屁來。」我下意識地摸了摸左臉頰的疤。
她看着前方,對我的說的話不置可否:「阿昭,巨鹿路有個書店你一定很喜歡,每次路過那裡我都會坐一會兒……去它那旁邊的餐廳吧,吃完附近的酒吧喝幾杯,再聊房子的事,好嗎?你幹嘛總是急匆匆的呢?六線城市不是很清閑嗎?你看你,不知道說什麼時就知道摸鼻子,還是小孩子一樣。」
這幾天,像料理後事一樣,我帶着某種嚴肅性像一個要遠航的水手那樣,留在岸上的親人告別。別過麗塔,第二天又急忙忙地趕回鶴崗,將我藏了很久的私房錢交給莎莎,留給她一個電話號碼,盡量輕鬆的說:「我會一直保持聯繫,如果萬一我失聯超過一個月,打這個電話。」事情就是這樣,我仍然停留在上述的漫不經心和隨風飄蕩中,但這些人是我的「岸」和「地基」,既然我斬斷錨鏈的手藉助了非客觀主義的力量,並不為人知。能否再靠岸,就只能繼續靠我的唯心與神秘力量了。捧着莎莎的頭,看着她怔怔的眼神,我輕鬆地開始說「正常」的出差事項:「這次去哈巴羅夫,不是砍幾百棵樟子松那麼簡單了。」「有多不簡單?」「嗯,主要是幫買家購進一些二手機器,相對複雜些,要保證回頭組裝順利,拆除時作業面比較狹窄。嗯,大概這樣子…工程上的事情,你懂的。」
第二天,從綏芬河口岸出關,還是兩兄弟越野車接上我。老二說明行程,先去辦簽證,連夜飛伊熱夫斯克;見到我們俄方的買手之後,我負責提供所淘物品信息,等俄方買手找到之後再確認即可。中間環節,譬如談價、付貨、包裝由他倆負責。和上次一樣,老大等買開始工作後,返回哈巴羅夫斯克,去一廢舊工廠拆除一台機加工設備用來包裝。一切順利的話,安排出關,我負責隨機應變。
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和俄方的買手交流,我把我在深圳看到的那個配件周圍的配件,以及中國自製的缺失的配件,儘可能準確地描述。當然,至於功能用途,和它的具體名字,我是不得而知的,或許這是我們跨國二道販子的通用慣例。我猜想是因為,如果你僅僅知道你買賣的東西是個廢品、破爛貨,那麼你就安全些,無論是在心理上和客觀事實上。哪怕上了法庭我也這麼說:「既然它像你們說的那麼重要,看管的人將負有主要責任,在某種程度上,它是被遺棄了而不是丟失了…」。我秉持這一原則,在描繪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上,既沒有添油加醋,也沒有過度想像。比如我會說,看起來應該是不鏽鋼,或者更硬的合金…直徑一米以內…嗯…差別不大,你的一肘,嗯,是的,一定耐高溫…抗風,至少300m…不不,在那個速度下再次點火…也正因如此,一個不期然的效果產生了:我們的交流沒有表達出需求方的迫切,供貨方也沒有流露出工作難易度的情緒。那幾個買手中的負責人,和我那之前見到的所有俄羅斯人都不一樣,身材矮小,戴着眼鏡,大部分時間雙手交叉抱在胸前,困惑的時候會一隻手抬起來摸着下巴上的鬍子,皺着眉簡單地詢問,點頭或者搖頭。
和你們想像的不太一樣,我們既沒有選擇在某處廢舊廠房、地下停車場、空曠的樓頂見面,就在伊熱夫斯克最熱鬧的大街上。談完了,一周後同樣時間地點見面。在一家商店的門口,我們三個看着俄方買手遠去的背影,開始了漫長的等待。為了渡過這難熬的一周答覆期,我們不能使用電子通信,不能使用信用卡,儘可能不在一處行動。我決定去趟聖彼得堡,這座城市是彼得大帝改革開放的傑作,被稱作「歐洲之窗」,在當時有點像我們的深圳。
-
連載中116 章

沈如燕顧司辰
不過看你剛才的情緒,好像並不是那麼高漲,你應該也是不願意讓她跟你回去,既然這樣的話,那如燕,要不你就繼續……」「別,我還沒有說話呢,你着什麼急。顧司辰連忙攔住孫逸軒,轉而認真的看着沈如燕,「你真的願意跟我回去了?」沈如燕堅定的看着他,「我孩子都在你手裡,我挂念他,必須得回去。聞言,頓時讓顧司辰有些始料未及,看着孫逸軒一副什麼都看透的樣子,不由得就明了了許多。孫逸軒正視着
-
連載中116 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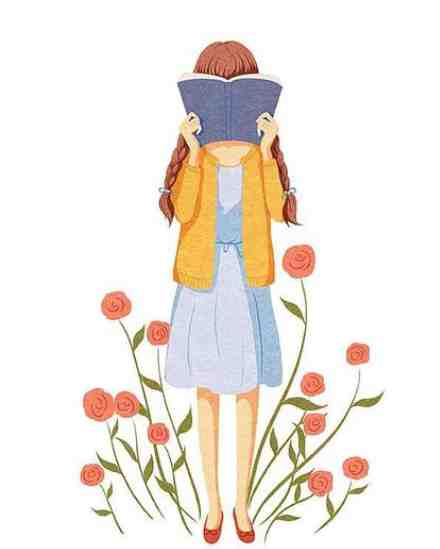
萬倍返現,大明星成了我的女友
上岸先斬意中人,我就被斬的倒霉蛋。天無絕人之路,天降萬倍返還系統,偶像美女大明星,公司御姐女總裁,鶯鶯燕燕的高分的美女,都成為我的舔狗。從此左擁右抱,腳踩財閥,掌摑二代,踏上巔峰!人生如此多嬌,我的腰!
-
連載中116 章

她頹廢又綺麗秦嬈靳司堯
秦嬈做過最大膽的決定,是睡服花花公子靳司堯! 她野心勃勃想要做他的獨一無二,妄圖讓他情難自持,步步沉淪。 她使出渾身解數,斗敗鶯鶯燕燕,回首來時路,步步血淚。 她以為她贏了,可直到最後才發覺,她不過是他深海里的一條尾魚。 秦嬈火了:「靳司堯,你玩我?」 男人欺身而上:「看清楚誰玩誰?」
-
連載中116 章

萬倍返現大明星成了我的女友免費全文閱讀
上岸先斬意中人,我就被斬的倒霉蛋。天無絕人之路,天降萬倍返還系統,偶像美女大明星,公司御姐女總裁,鶯鶯燕燕的高分的美女,都成為我的舔狗。從此左擁右抱,腳踩財閥,掌摑二代,踏上巔峰!人生如此多嬌,我的腰!
-
連載中116 章

陶真裴湛大結局
裴家被抄,流放邊關,穿成自殺未遂的陶真只想好好活着,努力賺錢,供養婆母,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。誰知慘遭翻車,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,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,和一雙看着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…… 外人都說,裴二公子溫文爾雅,謙和有禮,是當今君子楷模。只有陶真知道,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,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。 裴湛:「阿真。要麼嫁我,要麼死。你自己選!」 陶真:救命……我不想搞男人,只想搞錢啊!
-
連載中116 章

鑒寶大宗師
快遞員葉飛揚為了彩禮拚命工作,一遭覺醒鑒寶神技,窮小子的春天就要來了!
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